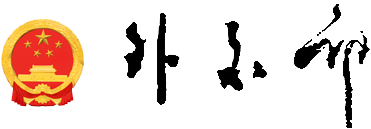主席先生:
人权会30多年前设立国别议题的初衷是敦促南非摆脱种族隔离制度,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。目前,国别议题却成为本委员会内最为政治化和最受争议的议题。自冷战结束以来,人权会已通过100多项国别决议,几乎全部针对发展中国家。人权会已成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“公审大会”。人权会造成的印象是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人权问题,而发达国家则是完美无缺的。
实际情况是,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尽善尽美。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世界人权发展进程之外。促进和保护人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和责任。一些发达国家将自己打扮成“人权法官”,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被告,颐指气使,发号施令,是人权会难以摆脱信誉危机,恢复生机与活力的根源所在。
主席先生,
长期以来,国别议题的审议之所以充斥政治对抗,是因为某些国家在借人权问题谋取政治私利。其手法和表现如下:
首先,一些国家总是好为人师,试图将自身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强加与人,以专制的方式在国际上推行“民主”。以自己设定的标准将各国划成三、六、九等,认定一些国家是“民主榜样”,另一些国家则是“无赖”。我做的都是对的,错的也是对的;你做的都是错的,对的也是错的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民主”。我们希望看到那些整天高喊“民主”口号的国家,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能切实做些带点“民主”味道的事。我在去年人权会曾表示愿意提供一面镜子,让那些国家在照别人的同时,也好好照照自己。在批评别人的时候,不妨先自我反省一下,充分利用中国代表团免费赠送的这面镜子。
其次,国别议题审议存在“强权即真理”的倾向。任何一个提案国,不论提案理由多么苍白,提案内容多么荒谬,只要具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,都可以通过公开或私下的威胁、利诱,拉足票数,强行通过。谁不听话,就威胁要实施经济制裁,再不听话就扬言要进行军事打击。人权会的国别提案成为强者的特权。人权会这一原本高贵圣洁的“人权殿堂”除适用经社会议事规则外,还适用“丛林法则”。无怪乎在这个议题下受到审议的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弱小国家,也无怪乎越来越多的受害国拿起“不采取行动”动议这一合理、合法的武器进行抵抗。
第三,模糊国别决议的标准。经社会1235号决议虽授权人权会在本议题下审议各国“大规模侵犯人权”的情势。但多年来,双边关系好坏、国内土地改革、民族和解进程等纯政治性的问题,都成为一些国家提出国别提案的借口,国别议题审议被“私有化”,其客观公正性受到损害。此外,国别议题下通过的决议很少形成协商一致。绝大多数系以表决方式强行通过,有的票数甚至十分接近。这表明,决议本身及其内容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。长此以往,不利于有关决议的落实,也有损人权会作为重要国际机构的权威。人权会已与促进国际人权合作的良好初衷在渐行渐远。人权会无疑需要改革,但仅仅改变人权会的名称显然是不够的。
主席先生,
今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,也是联合国的改革之年。国别人权议题是沿着过去的老路继续走下去,还是有所反思和改进,更好地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服务,是值得本届人权会认真探讨的问题。中国政府注意到,近来,不少国家提出为国别议题设定“门槛”,即规定只有当真正出现大规模、系统性粗暴侵犯人权现象,且在穷尽其它办法的前提下,才能提出国别决议。还有的国家提出彻底取消国别议题,增强人权技术援助议题的功能和范围。中国政府认为,上述建议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积极意义,都应受到人权会的重视。中国政府愿与各成员国一道努力,借联合国改革之年,深入探讨国别议题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式,共同推动人权会涣发出新的生命力。